霍雨浩失忆黑化:三生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0 00:01:59
【零点书库】 三生爱

现当代作家
小故事大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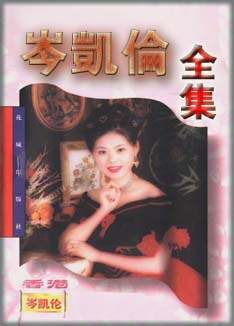
岑凯伦言情…
大功大过隋…
世界作家作
第二次世界
读者2011第
人生四大秘
寄秋言情小…

陈明娣言情…
《傅雷家书…
《青春的叛…
姚雪垠长篇…
霍桑探案小…
南湘野叟武…
《山海经》
席绢言情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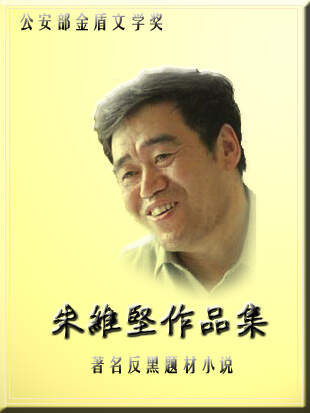
朱维坚作品












三生爱
叶文玲 女,祖籍浙江玉环。现任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洛阳师院兼职教授。1958年起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无梦谷》《父母官》《太阳的骄子》《秋瑾》《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等。小说集有《无花果》《心香》《长塘镇风情》等;散文集有《梦里寻你千百度》《写在椰叶上的日记》《艺术创造的视角》等40余种。
忆(一)
比情人更有缘
第一眼我就看见了她。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会在这儿——法国卢昂的这间酒店遇见她?!
一看清是她,我顿时又体会到那种如电击一般的头晕目眩。我敢说,世界上的任何人,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一遇上她,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立时黯然失色。
我相信这句话:最能感觉女人的美的,还是女人。
每逢和茫茫如约相遇或不期而遇,我总要想起这句话,尽管已上了年岁。不,应当说,也只有在与茫茫如约相遇或不期而遇时,我才想得起这句话。
她实在太俏丽了,这个茫茫!
“一个不折不扣的‘尤物’!”——很多人这样说过她。
茫茫,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字可以形容。
她穿一袭黑色晚礼服,正好站在酒店的那道旋转楼梯旁,一道猩红的照壁前。
我难以置信,竟是她站在那儿:穿一袭华贵的晚礼服,软滑而又挺括的黑丝绒质地长裙直垂至脚腕;大V字领,样式简约而前卫,窄肩的绊带斜斜而又恰到好处地滑落到肩胛骨,俏皮地露出冰肌玉肤的颈项和肩膀……除了胸襟上一枚水晶叶形花,别无装饰。
世上的邂逅多么奇妙,我到卢昂的造访完全是一种偶然而幸运的机缘。就像今晚,我们本来应主人之邀,到预订的饭店赴宴。主人临时改了主意,要重新安排在另一家莫泊桑饭店,说是因为考虑到我这个“顾问”的作家身份,而我,在感谢之余当然兴趣极浓。
据说,莫泊桑饭店不大名声大,在这个不是周末的傍晚也是人满为患,事先没订座当然就没戏。负责接待我们这个团的奈尔小姐,倒是一副每逢大事有静气的样子,在不慌不忙地叮嘱我们在这家非常堂皇的“五月花”酒店大堂稍等,便迈着她那驾云踩雾般的步子,悄然消失。
我也正是在“稍等”的时间超过了预计,才对这间相当华美又极有情调的“五月花”大酒店开始东张西望的。
这一望,就望见了茫茫。
虽然多年不见,我还是断定:是茫茫。肯定是她,不会是别人。
但我还是昏昏然而且有点忘乎所以。这得怨茫茫,是她的出现,使我的迷走神经总是要名副其实地“迷走”而出点问题。
我从一刹那的迷离恍惚中走出来,迎着她走去。
她显然不曾看到我,她根本不会想到我们又在这里相遇。
“我们能不期而遇,因为我们比情人更有缘!”——早在相识之初,她就这样对我说过。
伴随着清脆的话音的,便是一串同样清脆的笑声。这番话和这串清脆的笑声,曾不止一次撞进我的耳鼓。
俗话说:“美女瞳仁无他人”。对茫茫来说,此刻仿佛不仅仅是这个缘由,她好像在……
我马上发觉了她眼神里那种焦急的寻求和紧张的期待,这种焦虑不安的寻求和期待的眼神,是她一向就有的……
她不时朝那道旋转的玻璃门掠上一眼,因为焦急,她甚至斜斜着身子微踮着脚尖,这使她本就颀长而白皙的脖子更像一只欲飞的天鹅……
她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人。
我本来是径直迎上去的,稍一迟疑,才改了主意:我想从她背后绕过去,甚至还想玩一玩那些女孩儿们的把戏——用手掌蒙住她的双眼,然后再听她发出一声快乐的惊叫……
可是,我也是个不合时宜的急性鬼——穿行时,莫名其妙地被一个突然出现的行李车绊了一下,我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侍者丢下车子赶紧奔过来,惊慌万分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连连摇手表示没什么。
当我马马虎虎地揉了揉脚腕重新站起来时,就像鬼使神差,远处的情景已经换了人间天上——
茫茫被一个背影高大的洋男人揽在了怀里,那个背挡我视线的男人,旁若无人地将亲吻像雨点一样落在怀中的她身上……
这样接吻,当然是“鬼佬”!没错,这洋男人身驱高大,一头浅栗色的头发,一个颚骨宽大、唇髭漂亮的下巴,一件黑灰相间的条子衬衫束在一条乳白色的皮带中,这侧影,令人感觉像看到了一棵刚割完胶的橡胶树……
我顿时僵在那儿。这种场合怎好去打扰?尽管我千真万确断定这个男人怀中的女人是茫茫无疑,但是……
就在我怔忡间,脸孔红红的老小姐奈尔,终于又骤然出现了。她一如既往地以规范化而又不失迷人的微笑,用她那十分夹生的中国话,让我和我的同行们到不远的莫泊桑酒店去——自然,交道打通了。
莫泊桑,光凭这名字就令我荡气回肠,那是以往岁月中最让我着迷的作家之一。
我想,今晚的小宴,应该将这名字也一块吃到心里去,才对得起热情的奈尔。
我不懂法语。来法国虽已一周,但记住的单词也没超出如“喂、喂”(是、是)这个仅仅表示美好和服从的范围。这顿晚宴是对我们这小小代表团的欢迎宴,无论如何不能拂了奈尔小姐所代表的主人的盛意。
于是,我连忙招手翻译,请他向奈尔说明:我是不是可以稍等几分钟再过去,现在,我要先去与一位来自祖国的朋友打个招呼;这个朋友是刚才乍见、但已多年未见、刚才我们不期而遇、还没来得及打招呼;我如果不去招呼一声那就非常不应该;因为,对方不仅是一位朋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等于自己的……是的是的,无论怎么说都是我很关切的一个人……
天,翻译还没来得及将这意思翻完,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真是噜里巴苏十分讨人厌了!
噜里巴苏十分讨人厌的我,也终于周周折折地明白了奈尔那一说话就加上许多手势的回答:先去打个招呼、仅仅打个招呼、不耽误马上就开始的宴会;总而言之,这顿晚宴无论如何还是请你和大家一起到“莫泊桑”去吃、我们不能增加任何人也不可以减少任何人;总而言之,无论如何——奈尔在这时还举起一根葱白一样的指头加强示意——你得知道:这是一顿专为你这位顾问重选的地点、专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等同样噜里巴苏但却不讨人厌的奈尔,再次以一个标准的法国老小姐的迷人微笑,终于将她的意思反复表达完毕;而我也在稍稍定了神,礼貌地点了头、道了谢准备朝茫茫站立之处走去时……
嘿,红壁前,哪还有茫茫以及那个男人的身影!
我大失所望!我不明白,为何能在异国他乡有缘邂逅却无法相聚?难道,我和有缘的茫茫,现在已经不复有缘,而且注定了连相见都要打这样的“擦边球”?!
我喟然长叹,竭力劝说自己。不是吗,本来就没有相约,我们毕竟不是“一家人”,也不是“嫡系亲属”,尽管以往关系密切,但茫茫这几年的真实情况,我又所知多少?而且,毕竟没有招呼,又怎么断定刚才那个美女姑娘真的就是她?
不过,不管怎么自我排遣,我心里还是怅怅不已。
于是,当晚在莫泊桑饭店的晚宴,尽管是包括了蜗牛在内的地道而又丰盛的法国大菜,我却因为无心无绪而品尝不出一点什么特别的滋味。
旅行是快活的事,旅行也最容易疲劳。前几天都是早早洗漱着枕便睡,但这天夜里,却怎么也睡不着。安静整洁的房间,换洗过的雪白洁净的床单和枕套,有一股淡淡的桅子花味,崇尚香水且种类繁多的法国,在诸如此类的铺陈中果然都有体现。
我却依然辗转多时而无法安眠。
胡思乱想中,纠缠于心的都是有关茫茫的一切。准确地说,应是有关她母亲和外婆的一切。
难道命运和人生经历也会随外貌遗传?茫茫的母亲和外婆,都是旷世美女,同时也都有着旷世美女的红颜薄命。
母亲早就告诉过我:二十年代末,茫茫的外婆,就曾以她的出奇“故事”和绝世美艳,曾教故乡的小镇天翻地覆。
……我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之中——
我掉入了一个深深的漩涡,浊水万丈,恶浪滔天,一艘黑色的铁壳船迎面开来,从我头顶隆隆开过,顷刻之间就要将我绞成肉泥。我不会游泳,周围没有任何可以救我之物,更不用说救我之人。
我伸手乱抓,可四下全是一片冰凉的水,我能做的,只是一声声绝望的呼喊!
我惊醒了。
心如撞鹿,冷汗淋漓。当明白自己刚才不过是做梦时,竟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惊喜。
故乡的老人总说人梦见水是好事,梦水,要发“水花财”。
是这样么?我常常梦见水,可它从来没有应验过。对我来说,梦常常是现实的一种反证,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叠而已。
我越发睡不着。在这时候,最好的方式是索性披衣坐起,让梦境回归现实,哪怕仅仅是回忆的现实。
“半掩门”母女
六十年代初,我踏上了人生旅程中的第一个驿站——青岛。
夜色苍茫中,我随着来接我的要成为我丈夫的滨声仓惶地走,高一脚,低一脚,细细的微雨中,两人共撑一把黑色的小阳伞,我的浅绿葡萄叶的花布连衣裙和脚上的布鞋,溅满了泥点。那情景,压根儿不像来结婚而是来逃难。
婆家在火车站附近。当我一脚迈进了一个大杂院时,这个原本很为我仰慕的胶州湾海滨城市居民区,却以一种我完全没有料到的面貌,呈现眼前。
婆家的大杂院是沿着一座大天井砌的四围两层楼,一门一窗便是一户,像蜂窝一样。夜深的幽微灯光中,一时看不清有多少户人家拥塞在这两层楼的院中。
第二天一早,我从婆家的窗户中,张望这一只只炊烟袅袅的“蜂窝”,愣愣地看着一个个在院内活动的身影。
婆婆和公公在鸽子窝似的楼屋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与物质有关的一切都贫乏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可是,生活中只要有一点点喜乐,仍会像连日的雨花一样四处迸溅。
穿着打补丁裤子和我结婚的滨声,只有脚上的鞋子是新的——那是我亲手做的。眼下的我和他,在喜洋洋的婆家,成了“富贵闲人”,傻乎乎而无事可为地看着两个老人里外张罗。
公公婆婆拿着凭“结婚证供应”的两斤喜糖,摆在炕桌上像数珍珠一样分成小堆,一边念叨着:陈家的、章家的、龚家的、邱家的、水果林的、烧鸡铺的……
喜糖的分发对象是大院中的邻居,“堆儿”的大小,是根据这家孩子的多少。
“真寒碜人,就那么几颗糖,他爹,待会儿给人家时你可得跟人说明白,不是咱不割舍的,一共就让咱买这么一丁点东西,唉唉……”婆婆不住唠叨着,一会儿从这堆上减下两颗,一会儿往这堆上增添一颗。婆婆摆弄停当后,听话的公公就用裁好的一张张红纸包好。
公公耳朵背,常常动用自己发明的“扩音器”——以一只手掌遮耳,才听得见人说话。但婆婆唠叨的内容他好像不用听也明白。突然,他想起了什么。
“忘了给班家吧?添上她一份……”
“给她?给那个‘半掩’家?”婆婆反问。表情和语气都表明:她不是疏忽。
公公很不以为然。“怎么不给?给!人家也是一户嘛……”公公说着,不由分说地从还没分完大堆里抓了一把。
“要给也不用那么多,她家又没小嫚……”看得出来,婆婆明显的不怎么喜欢这个叫什么班家还是半家的,她硬是从那堆儿里又扒拉下几块,一边咕哝说:“原都不够分……”
“你都不想想,班家的跟我们滨声家的还是浙江老乡哩!”公公见婆婆仍不肯通融,叹息一声,摔了手,扭头就出去了。
没多大一会儿,公公又转回来了,他的手中奇迹般地捧了一小包……糖!
这情景使大家都喜出望外。婆婆一个劲地追问公公是牺牲了家中别的什么才开来了这个后门?公公瞪她一眼,皱着眉,恼怒地低吼了一句什么。
我没有听懂。公公婆婆说的那些胶东口音很重的方言,我常常不能完全听懂。
婆婆不再咕哝,仍然将“班”家的那一份抓了出来,分门别类地放在一角。
寒伧而简朴的婚礼举行那天,大院里的孩子嘻嘻攘攘聚集到我们家门前,虽然每家已按份分发过喜糖,孩子们还是要到办喜事家的人家再抢几颗糖,这也是一种讨彩。喜笑颜开的公公,差点没让那帮晒得泥鳅似的蛮小子给掰坏了指头。
没来凑热闹的,只是班家。本要送去的糖,被隔壁邻居告知“她们娘儿俩出门了,到医院去了”而暂时搁置。
忙乱中顾不上许多细节。
三天后的傍晚,滨声正想带我到海边遛弯,公公曼声吩咐道:滨声,快把这给班家送去吧!都几天了……
我们顺着他努嘴的方向一看,终于瞥见那个小小的红纸包,依然静卧在壁橱上方。
丈夫一向很遵从公公的主张,大概觉得这几颗糖太小小不言了,迟疑而为难地说:这点点东西……
公公嗔怪地瞪他一眼,固执地说:不在东西多少,这是礼数,你和你媳妇一块送,好歹她们也是老乡……
“好吧,好吧……”
我糊涂了,小声问滨声:“这家人是姓‘班’还是姓‘半’?还有这么奇怪的姓……”我住了口,因为丈夫重重地按了一下我的手腕。
班家的木门与大院内多数人家一样窄小而破旧,轻轻一推就开。
进门后才发现窗边吊着一盏度数极低的灯,窗框旁虽然罩了一张白纸反光,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依然十分昏暗,好大一会儿,我才大体辨得清眼前的物事。
屋子虽小,却十分清洁,桌椅板凳全都揩得干干净净,就连板壁窗框也擦得纤尘不染。只是,屋子实在太小了,中间又被一张桌子、桌子又被一堆山也似的火柴盒子占据了全部地场,周围的许多物事好像都被遮掩了。
就从这堆小山也似的火柴盒中间,伸出了一个梳髻子的花白脑袋,大概没有想到是我们,班家的这个梳髻子的老女人“哎”了一声,连忙站起,热乎乎地手忙脚乱地一边招呼,一边试图给我们腾出坐的地方来。
滨声连忙表示不必客气,说明来意,放下糖就要走。
“多谢多谢,你爹总想着我们!”老女人忙着从壁角的床下抽出凳子,连连说:“忙什么呢,滨声,坐,坐呀,难得回来一次,就在我们这里嬉嬉一歇歇,嬉嬉一歇歇……”
“嘿,坐一会儿也不会矮了你,化了你,怕什么呢?!”随着话音,突然从我眼前亮起一道月光——一张雪白而姣美的脸庞,鬼使神差般从老妇人的背后,在一道半截的蓝印花布的帘子后边出现,一对水汪汪的杏眼在蓬乱的额发下,讥嘲地半眯着,飞速地射向我们,亮亮的眼瞳,在我身上逡巡了一圈又一圈,接着又用鼻子轻轻哼着。“到底是南方人,小模样真不错,嗯,这么小,够不够结婚登记的年龄?”
我惶惑地看着她,不知说什么才好。
她不理会滨声,突然又朝我说:“喂,你叫什么名字?知道么,没听你公公说么,你和我妈是老乡呢!不信你问问……嘿,滨声,现在是大教授了不是,架子大了,不爱搭理我们这小民百姓了?”说着,她又眯着眼在我脸上“剜”了一圈。“滨声,你可真有本事,骗得来这么俊的南方小媳妇……”
滨声脸一红,立刻期期艾艾,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与眼前的这个俊俏女子多说话,但又想不出托词马上告辞。
“人家是客人,婧婧,你这是做什么……”老女人沉下脸喝住了年轻女子,依然客气地招呼:“滨声,快坐快坐……”
滨声终于想出了借口:“哎哎,大娘,有个同学同我们约过了,让我们过去呢!不坐了,不坐了!”不会撒谎的他,连脖子都红了。
“拿什么架子,哼!”那个被老女人叫做婧婧的年轻女子一听,立刻摔下脸,像刚才一样飞速消失在那道半截的蓝印花门帘后边……
那老女人倒也不强留,立刻很解人意地说:“那是,那是,快去吧,别教人家等着,咱这儿离得近,早早晚晚都能过来嬉嬉的,跟你爹娘说,谢谢了,哎,那么惦记我们……”
走到门外的马路上,丈夫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大气。
我好奇极了,一百个问号霎时堆集心头。
那时的我,虽然已经发表过几篇小说,却不敢将这归结于小说家的敏感。
但是,关于“班家——婧婧”的一切,就此引我好奇顿生。公公、丈夫还有这个婧婧都说老女人和我是“浙江同乡”,更令我大感兴趣。从她明显的故乡口音和最后的那几句“嬉嬉、一歇歇”,我判断出这真是我们老家的方言,这么说,她不仅是我的大同乡,还可能是很小范围的老乡。
“滨声,我看,那个婧婧很爱你呢,她看你的目光,真像是无奈分手的情人似的……”
“什么话!”滨声涨红了脸,立即否认。“她对谁都是这样……哎,不过,我们倒真是初中同学,她比我低一届,是外来户,我上高小时,她和她母亲才搬到我们这大院……咱爹早就认识她母亲,是在大港码头认识的,爹那会儿在码头看仓库,大概是鬼子投降那时候吧?也许是稍早一些些,我不清楚,反正那会儿乱七八糟的,日本鬼子都在撤,那班大娘,哎,就是婧婧她妈,抱了个四五岁的女孩,对,就是婧婧,听说她妈当时是有意不肯上船还是被人拉下的,我也不太清楚,听爹说好像是被人遗弃了还是怎么的……嘿,她那时还会讲几句日语呢!原来她们是住在外头的,后来又遇见咱爹,才又搬到咱这个大院,这里的房租便宜。后来,咱爹退休了不是当着居民小组的什么委员么,见她们母女生活困难,就常给她母亲介绍个糊火柴盒子之类的活,挣几个小钱对付过日子……所以她妈总对咱爹有点感激涕零的,嘿,有时还惹得咱娘老大不高兴,你知道咱娘是小心眼……”
“这我知道。我到现在也没听清,她们是姓班吧?娘为什么叫她们是‘半掩’家的?”
“是姓班。婧婧的学名叫班小诺。嗯,‘半掩’么,就是,就是‘半掩门’,你知道吧?北方话,当然是不好的称谓,院子里的人都说婧婧母亲以前是不正派的女人,所以全大院的人都有点瞧不起她们,还说婧婧是外国种呢!……”
“真是这样?”
“乱猜罢了!”
“婧婧父亲呢?”
“不知道,我从没见过。反正她母女俩的行为有点神神秘秘的,也不和院子里的人多说话,咱爹可能有点知道底细,可咱爹是厚道人,从不多说别人……”
“这个婧婧长得真漂亮!”我由衷地赞叹,“你真傻,婧婧要是真和你找了对象,你可是艳福不浅!”
“什么话!她后来压根儿不上学了,我离家上大学后就不知道她的事,哪里会同她……”滨声很认真地辩白道:“我们这个大院几十户人家,邻居也不过是邻居而已,彼此有点知道,却不是知根知底的,不像你们南方小镇,上下三代都一清二楚,就像你在小说里写过的那样:‘小镇上传消息,比电报还快’……”
“别打岔。我是说,这婧婧的母亲,真是从我们那里过来的么?咱爹真知道她的来历和细情?”
“不,不很清楚的,我们这里,说是邻居,平日是谁也不管谁的闲事的,我只知道婧婧初中只上了两年就休学了,嗯,我和她,虽然同一个大院住,也在一个学校上过学,可十多年加起来没说过多少话……”
“这么假撇清干什么?”滨声着急分辨的样子令我好笑,我知道他这人不会说假话,但我还是要逗一逗他。而且,婧婧刚才的言行举止虽然有点尖刻,但她真的特别漂亮,说实在,我至今还没见过比她更俊美的姑娘。她母亲也是,这母女俩的眉眼五官,特别是那双得兼“凤眼”和“杏眼”之美的眼睛,朝人一望,真是风情万种,大有教男人们招架不住的勾魂摄魄的美丽。
我一点不夸大,这母女俩,真是美丽到了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地步,那班大娘虽是老人,按我们南方的美人标准,也够得上俊俏透顶,除了脸色稍过苍白外。可是,也许正是这出奇的苍白,才惹动我由衷的赞叹——因为,苍白和苍白关联的凄美,一向使我动心。
“哦,这婧婧和她母亲,长得可真是,是的,说像又不完全像,可都那么美丽,不,准确地说,是妩媚,我觉得婧婧有点特别……不,我更喜欢她母亲的那种清秀脱俗的、静静寂寂的妩媚,她年轻时准是个绝色美女……婧婧么,有点洋气也带点野气,没和她好,你真是呆犊一个……”我自言自语。
“哎,你问这问那,原来是怀疑……”滨声认真得又像生了气,等他明白我是在开玩笑时才如释重负地笑起来。“你也真是……怪不得说写作的人都有点小神经……”
“嗯,我问你,婧婧后来为什么不去上学呢?”
“当然是因为生活困难想早点工作吧。”
“你不是也享受助学金么?她为什么不去申请助学金呢?”
“这?我哪里知道……当时听说她好像去什么文工团了……”
“现在呢?现在她做什么?”
“我哪里知道?我不是也离家好多年么,听说好像也在码头的什么单位……
我沉默不语,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和想象中。婧婧和她母亲的出奇美丽和神秘身世,特别是她对人说话的神情,在我心里激起一片分外好奇的连漪……我突然想起来:她们母女之所以容貌姣美且又特别神似,还因为她们脸上都有一对大而深深的酒窝,不同的是,女儿的眼睛有一种撩人的妩媚,而母亲则有一颗美丽的小痣,俏皮地跳在左眉上……
美人微疵才是真美!
公公可能知点内情,但他耳背得厉害。平日,我们与他交流总要提着嗓门才能对话,就这,也常常被他听岔了意思。因此,除了肯定婧婧现在是在大港码头的下属单位上班以外,早已退休的公公也说不出有关婧婧母女更多的近况和内容。而小心眼儿的婆婆,却总是时不时的从左邻右舍的“小广播”中听到一些传言。不久前,她又听到了一个秘密,言之凿凿地说:前些日子婧婧母女去医院,是“老的陪着小的偷偷去做‘人流’了……”
为了证实自己说的没错,婆婆加重了语气:“老葛家的可是不会屈枉她的,你不知道人家老葛媳妇就在那家医院当护士长的,现在,满院的人都知道了,他爹,你没听说?我不信你真没听说……”
公公含混地应了一声,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婆婆乘机大发感慨:“什么样的娘生什么样的闺女,那娘儿俩,没治了,真没治了……”
我好像猜测到了一点什么。
因为居住空间窄小,大杂院的人家,总是将很多吃喝拉撒睡的私人生活家务内容展现在院子里。令我奇怪的是,这个大院惟班家母女例外。不知为何,她们很少在院子里出现,婧婧和她母亲也很少与别人打交道。这在一个连解手撒尿都在一个公用茅房的大杂院居住者来说,真是与众不同。特别是班大娘,整日在家忙着糊那如山堆积的火柴盒,足不出户。
于是,渐渐地,进出大院时,敏感的我,虽然时时感觉着楼下某个角落的门帘后,有双不无友好而略带哀怨的眼神的注视,但是,对神神秘秘的婧婧和她母亲的话题,却不能不随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进程而淡然。
日子飞逝,我们很快度完了半个月婚假而终于要离去了。这天傍晚,我照旧来到海滩遛弯,和往日不同的是,这天仅仅是我自己——滨声遵公公吩咐到亲戚家送什么物件去了。
半月下来,我对这片海滩已是熟门熟路,特别是那处在黄昏时分露出海面的礁岩,早已成了我每天晚上的消闲之处。
那个年月,青岛最教我眷恋的,就是蓝天下的大海,就是这海天一色的有着黑森森礁岩的海滩。
海滩寂寂,蔚蓝色的海浪,裹着白花花的裙边扑将上来,就像是害了单相思的女孩,执拗地一次又一次地扑向意中的情人,亲昵地不厌其烦地拥吻着,她一无所有,唯有这拥吻是如此固执而甜蜜……
造物主对人还算公平。这处近在咫尺的寂静而不无美丽的海滩,就是对世世代代居所拥塞的人们的补偿吧。要是没有它,我可怜的住了一辈子大杂院的公公婆婆们,不是连个透气的地方也没有么?
“嘿,好悠闲呀,看什么呢?”身后传来熟悉的语声。
是她,婧婧!弹跳般走近来的婧婧,步子轻盈又优美。
夕阳中,她那略略苍白的脸庞透出了一抹粉茸茸的浅红,那张美丽的脸于是更加千娇百媚。由于夕阳的点染,她的头发泛出一圈似金非金的浅棕,这种颇显华贵的发色在如今极为流行,年轻的时髦女孩,差不多十之八九都去染过这种“外来色”。可我敢说,从没有一头秀发,能够与我当年在海滩看到的婧婧相嫓美,那是蓝海衬出来的真正的自然美色。
我从礁岩上站起来,面对她,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有点惶恐。
她轻盈地跳身过来,一坐到我身边,就不由分说地一把将我按了下去。
“坐嘛,再坐一会儿。滨声没同你一起来么?他怎么不陪你?真是的!说到底,山东人都是老粗,指望他们知冷知热地疼媳妇,没门!”
我一时语塞。说实在,至今我与她还没有正式交谈过,我略显窘迫地微微一笑,不知道与她说些什么才好。
“你们快走了吧?明天就走?到哪里?还去河南?内乡?这样的名字?嘿,什么鬼地方,听都没听说过!你怎么会答应跟他去那样一个地方?别走了,青岛多好呀,青岛再差也是大城市,你跟他去那儿干什么?要我,宁肯在青岛要饭也不去!”她滚珠连串地说着,脸上掠过因话语而改换的表情。那表情也因她急速的语声飞快而生动,杏仁般的眸子在暮色中闪闪星亮,那张美丽的脸,在斑斓的夕照中简直是五彩流光。
对于她的话,我依然不知如何回答,也无法回答。而且,我发现,婧婧说话语速极快,无需或者可以说根本无视对方作什么反应,那双瞳仁乌亮眼白有点泛蓝的眼睛灼灼地瞪着你,眼神却不住地游动,我忽然感觉她好像有点病态,至少眼神透露出某种病态的信息。
我为这个发现吓住了,心情突然一阵紧张。
“喂,我说,滨声对你很好吧?他可是个好人,我们山东人就是爱讲义气……”她亲亲热热地挽着我的肩膀,唇线分明的菱角嘴凑近了我的耳朵,轻轻吹出的气,教我的耳根痒痒的。“你知不知道,我和滨声原来很要好哩,要不是他毕业分配去了那个鬼地方,我一准会嫁给他!真的,前些年,我可是真心真意看中了他,他是我少女时代的第一位白马王子,可滨声这人有点‘潮巴’,真的,大‘潮巴’一个,我对他动心思,他一点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时,追我的男同学都可以编成一个排了,他们成天为我打架,我们的一个音乐老师,为了我都差点跳楼自杀,你信不信?”
我想,我应该信。
她那么近近地挨着我,我才发现:要说婧婧也有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她虽然脸色很白,但脸颊和鼻翼两旁有着一些细小的雀斑,当然,若不是近观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我随即想起了一句俗话:美人可比美玉,白玉无瑕,有微疵的美人却比无瑕的白玉更耐看。她的这些细小的雀斑,好像就是为了反衬她的美白,就像她母亲眉角的那颗小痣,不但无损于美丽,还增加了许多妩媚。
面对她滚珠连串的表白,我不能一言不发,于是便点点头。“是的,婧婧,你很漂亮……”
婧婧眼睛一闪,开心地笑了起来。“是么,我真像你们南方女孩那样漂亮?嘿,你知不知道我们大院里那些人坏得很,他们给我起了许多外号,你可别听他们瞎掰乎,嗯,我们这大院,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些混账王八蛋!也就你们家,嗯,就你老公爹和滨声是好人,你知不知道,有次滨声为保护我,还曾跟一个想欺负我的小流氓打了一架,门牙都差点打掉了!真的,他没有对你说过吧?他肯定不好意思说的,你可别问他……”
我当然不用问也不会问。婧婧虽然坦率得令我吃惊,但我也推断出有一些“情节”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真实,例如滨声为她打架和“门牙”之类的事。
我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喂,我问你,滨声他是不是结婚当天就……就对你‘那个’来着?我们山东人,一个个人高马大的,又那么大岁数了结婚,还不是……急猴儿似的,是不是……”
她都说些什么呀……我的脸红到了耳根,不能不站起身来:“对不起,婧婧,我得回去了,今晚还得收拾行李……”
大概因为我的矜持,太辜负了她的美意吧,婧婧有点着恼,立刻很不友好地甩了手,掠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背转身子,两手抱膝,语气冰冷而不耐烦:“你这人……好好,走吧,走吧,我还有约会……”那神情,霎时间就与刚才判若两人。
勺港的婼婼
奈尔小姐早上准点来到。我们一块吃了早餐后,便驱车前往展览中心所在地。
这次出访法国,是省对外友协的一项文化交流的任务,我们将在此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首先要举办一个包括书画展出、然后是音乐舞蹈演出的“西子文化节”。
“友协特邀理事”是我最近的一个“虚职”,所以我当时的身份是代表团的“顾问”。我是为了搜集眼下要写的一部传记文学的资料接受这项兼差的,书中主人公曾经在法国生活多年,所以非来这儿不可。因此,这项兼差于我,是一举两得。
展览中心和卢昂所有的场所一样,美丽而洁净。展馆在花园中央,被一片草地簇拥,绿茵茵的草地,嫩气生香,远远望去,白色的馆舍就像碧绿的江面飘着一片白帆。
早在我们抵达前,奈尔小姐已替我们选好这个展览场所。她说我们带来的字画,昨天也都在室内悬挂完毕。这一次,我们这个团所带的,大多是文联和画院提供的我省当代书画家的作品,虽不属国家列名禁带的大家名作,却是非常有水准的。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了奈尔小姐的精心,她总是时时表示对中国文化懂行和亲昵——她让人在展厅门口上方,横悬了两条金色的龙,展厅两侧又吊起了四盏有着双喜字的大红灯笼,对于一个书画展览来说,这装饰称不上精致更不能算协调,但却有中国式的喜气洋洋。
书画展虽然只是整个活动中的一项,但参展的书法绘画,大多是我省首屈一指的年轻美术家的作品,这其中,尤以“水乡画家”之称的立舟的作品——《水乡江南·四季系列》最为醒人耳目。立舟因独特的表现手法名声鹊起,多年来在全国美展以及其他活动中屡屡获得奖项。
“西子书画展”在一片掌声中开幕。
如果不是眼前的“观众”多是金发碧眼,我并没有感觉这是在国外。虽然,刚才出了点差错,一些细节安排也不是那么合规合矩,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像模像样的,起码展出的作品很能体现中国书画的品位。因而,虽然举办地是在法国的卢昂,我的感觉好像是在国内的某个城市又一次歆享了中国文化的大餐。
向以浪漫著称的法兰西,能否领略中国“西子”文化的别样情韵呢?
中西文化的不同在细节中也时时显现——他们剪彩用的是一条一指宽的细带而不像我们大手大脚的整匹红绸红缎;主持人的开幕词没有虚夸和客套而只是一两句很幽默风趣的“介绍”;而观众当然更不一样——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多是来者如意的样子。有几对看得一时兴起的年轻情侣,看着看着,就旁若无人地相拥而接起吻来。
法国人在任何时候总有无限的浪漫。
我们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则来自省文艺界的四面八方,有几位是音乐舞蹈界人士,他们的展演节目,在另一个剧场安排,包括开幕式。因为难以分身,我和作曲家出身的团长各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与对方一起尽量安排好这次画展。
访问中的参观,无疑是代表团最感兴趣的。
天淡云低,细雨飘洒,卢昂的秋天竟如杭州之春,时晴时雨,极有诗情。
细雨如诗中,我们在带路人的引领中走向一所博物馆,那馆舍无例外地和这座城市一样古老而整洁。除了第一展厅的橱窗摆了一些古物外,其余无例外是宗教内容的油画。
刚刚走出博物馆,换了一身米白色衣裙的奈尔小姐,手持一柄长伞,像一只秋风中飞翔的白鹳,脚步飞快地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发丝上落满雨珠的奈尔,指着天色,皱眉耸肩地叹气说:天气太糟糕了,她想稍稍改动我们的参观内容——问我们是愿意接着冒雨去看当地的一些纪念地还是去逛商场?
当我听说贞德的纪念雕像以及被处死的行刑场就在附近时,不由得惊喜万分。我直截了当地对奈尔表示:对于我来说,如果能够看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地,哪怕再淋雨也没有关系,至于商店那是可去可不去的。
说话时,我心头旋风似的刮过了昨晚的梦境,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的愿望,真的完全是由于那个世人所敬仰的贞德,还是别的什么。
奈尔听清了我的要求后,诧异而不无惊喜地说:她非常尊重我的意愿,因此,她可以马上去找一名懂法国历史又能说中国话的大学生来陪我,这样,就能尽情介绍有关贞德的美丽而壮烈的史迹……奈尔再三说,她还认识好多“中国通”,一定可以找到我所需要的陪伴者。
我知道她误会了。我不过是一名游客而并非专门的研究者或专家,我诚恳谢绝了她的好意。我说:绝对无需再找什么人专门陪我,如果其他人都愿意逛商店,我就自个儿去哪个地方转一圈就行。我请她放心,我说我还知道下一步的集合地,我绝对会追上她带领的那支对法国商店特别爱好已经走得松松散散的参观团。
我拖着走得发酸的脚,在街角的长条木凳坐下,凝视着离我咫尺之遥的贞德雕像。
思绪一如秋风翻卷。此时,我才明白:刚才,与其说是被贞德之死的壮烈所感,还不如说是她那“处死方式”的惊世骇俗使我感怀不已——在中世纪的这个小城,一个曾为国家赴汤蹈火的年轻女子,在大庭广众中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
历代中国女子,与此壮烈死法相似的,都有谁?
哦,秋瑾,大义凛然的秋瑾当然算一个。毫无疑问,她一直是我无比敬崇的女侠。秋瑾慷慨赴死的一幕,曾使为其作传的我热泪涟涟不能自己。
其他呢,当然,当然还有很多,古今中外许许多多革命烈士……
且不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她们,大家都熟悉。我想的是小人物,想想那些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惊世骇俗的普通百姓平凡女子……
就此来说,茫茫的……对,茫茫的外婆也属这样一个女子!
怎么又想到了茫茫?至此,我才明白;今天的恍惚的思绪,全在于昨夜不宁的梦境。
不不,也许该说,全在于昨日与茫茫不期而遇而又未曾真正相见。
结婚两年后,我回到老家分娩。
现当代作家
小故事大智
岑凯伦言情…
大功大过隋…
世界作家作
第二次世界
读者2011第
人生四大秘
寄秋言情小…
陈明娣言情…
《傅雷家书…
《青春的叛…
姚雪垠长篇…
霍桑探案小…
南湘野叟武…
《山海经》
席绢言情小…
朱维坚作品
三生爱
叶文玲 女,祖籍浙江玉环。现任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洛阳师院兼职教授。1958年起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无梦谷》《父母官》《太阳的骄子》《秋瑾》《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等。小说集有《无花果》《心香》《长塘镇风情》等;散文集有《梦里寻你千百度》《写在椰叶上的日记》《艺术创造的视角》等40余种。
忆(一)
比情人更有缘
第一眼我就看见了她。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会在这儿——法国卢昂的这间酒店遇见她?!
一看清是她,我顿时又体会到那种如电击一般的头晕目眩。我敢说,世界上的任何人,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一遇上她,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立时黯然失色。
我相信这句话:最能感觉女人的美的,还是女人。
每逢和茫茫如约相遇或不期而遇,我总要想起这句话,尽管已上了年岁。不,应当说,也只有在与茫茫如约相遇或不期而遇时,我才想得起这句话。
她实在太俏丽了,这个茫茫!
“一个不折不扣的‘尤物’!”——很多人这样说过她。
茫茫,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字可以形容。
她穿一袭黑色晚礼服,正好站在酒店的那道旋转楼梯旁,一道猩红的照壁前。
我难以置信,竟是她站在那儿:穿一袭华贵的晚礼服,软滑而又挺括的黑丝绒质地长裙直垂至脚腕;大V字领,样式简约而前卫,窄肩的绊带斜斜而又恰到好处地滑落到肩胛骨,俏皮地露出冰肌玉肤的颈项和肩膀……除了胸襟上一枚水晶叶形花,别无装饰。
世上的邂逅多么奇妙,我到卢昂的造访完全是一种偶然而幸运的机缘。就像今晚,我们本来应主人之邀,到预订的饭店赴宴。主人临时改了主意,要重新安排在另一家莫泊桑饭店,说是因为考虑到我这个“顾问”的作家身份,而我,在感谢之余当然兴趣极浓。
据说,莫泊桑饭店不大名声大,在这个不是周末的傍晚也是人满为患,事先没订座当然就没戏。负责接待我们这个团的奈尔小姐,倒是一副每逢大事有静气的样子,在不慌不忙地叮嘱我们在这家非常堂皇的“五月花”酒店大堂稍等,便迈着她那驾云踩雾般的步子,悄然消失。
我也正是在“稍等”的时间超过了预计,才对这间相当华美又极有情调的“五月花”大酒店开始东张西望的。
这一望,就望见了茫茫。
虽然多年不见,我还是断定:是茫茫。肯定是她,不会是别人。
但我还是昏昏然而且有点忘乎所以。这得怨茫茫,是她的出现,使我的迷走神经总是要名副其实地“迷走”而出点问题。
我从一刹那的迷离恍惚中走出来,迎着她走去。
她显然不曾看到我,她根本不会想到我们又在这里相遇。
“我们能不期而遇,因为我们比情人更有缘!”——早在相识之初,她就这样对我说过。
伴随着清脆的话音的,便是一串同样清脆的笑声。这番话和这串清脆的笑声,曾不止一次撞进我的耳鼓。
俗话说:“美女瞳仁无他人”。对茫茫来说,此刻仿佛不仅仅是这个缘由,她好像在……
我马上发觉了她眼神里那种焦急的寻求和紧张的期待,这种焦虑不安的寻求和期待的眼神,是她一向就有的……
她不时朝那道旋转的玻璃门掠上一眼,因为焦急,她甚至斜斜着身子微踮着脚尖,这使她本就颀长而白皙的脖子更像一只欲飞的天鹅……
她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人。
我本来是径直迎上去的,稍一迟疑,才改了主意:我想从她背后绕过去,甚至还想玩一玩那些女孩儿们的把戏——用手掌蒙住她的双眼,然后再听她发出一声快乐的惊叫……
可是,我也是个不合时宜的急性鬼——穿行时,莫名其妙地被一个突然出现的行李车绊了一下,我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侍者丢下车子赶紧奔过来,惊慌万分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连连摇手表示没什么。
当我马马虎虎地揉了揉脚腕重新站起来时,就像鬼使神差,远处的情景已经换了人间天上——
茫茫被一个背影高大的洋男人揽在了怀里,那个背挡我视线的男人,旁若无人地将亲吻像雨点一样落在怀中的她身上……
这样接吻,当然是“鬼佬”!没错,这洋男人身驱高大,一头浅栗色的头发,一个颚骨宽大、唇髭漂亮的下巴,一件黑灰相间的条子衬衫束在一条乳白色的皮带中,这侧影,令人感觉像看到了一棵刚割完胶的橡胶树……
我顿时僵在那儿。这种场合怎好去打扰?尽管我千真万确断定这个男人怀中的女人是茫茫无疑,但是……
就在我怔忡间,脸孔红红的老小姐奈尔,终于又骤然出现了。她一如既往地以规范化而又不失迷人的微笑,用她那十分夹生的中国话,让我和我的同行们到不远的莫泊桑酒店去——自然,交道打通了。
莫泊桑,光凭这名字就令我荡气回肠,那是以往岁月中最让我着迷的作家之一。
我想,今晚的小宴,应该将这名字也一块吃到心里去,才对得起热情的奈尔。
我不懂法语。来法国虽已一周,但记住的单词也没超出如“喂、喂”(是、是)这个仅仅表示美好和服从的范围。这顿晚宴是对我们这小小代表团的欢迎宴,无论如何不能拂了奈尔小姐所代表的主人的盛意。
于是,我连忙招手翻译,请他向奈尔说明:我是不是可以稍等几分钟再过去,现在,我要先去与一位来自祖国的朋友打个招呼;这个朋友是刚才乍见、但已多年未见、刚才我们不期而遇、还没来得及打招呼;我如果不去招呼一声那就非常不应该;因为,对方不仅是一位朋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等于自己的……是的是的,无论怎么说都是我很关切的一个人……
天,翻译还没来得及将这意思翻完,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真是噜里巴苏十分讨人厌了!
噜里巴苏十分讨人厌的我,也终于周周折折地明白了奈尔那一说话就加上许多手势的回答:先去打个招呼、仅仅打个招呼、不耽误马上就开始的宴会;总而言之,这顿晚宴无论如何还是请你和大家一起到“莫泊桑”去吃、我们不能增加任何人也不可以减少任何人;总而言之,无论如何——奈尔在这时还举起一根葱白一样的指头加强示意——你得知道:这是一顿专为你这位顾问重选的地点、专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等同样噜里巴苏但却不讨人厌的奈尔,再次以一个标准的法国老小姐的迷人微笑,终于将她的意思反复表达完毕;而我也在稍稍定了神,礼貌地点了头、道了谢准备朝茫茫站立之处走去时……
嘿,红壁前,哪还有茫茫以及那个男人的身影!
我大失所望!我不明白,为何能在异国他乡有缘邂逅却无法相聚?难道,我和有缘的茫茫,现在已经不复有缘,而且注定了连相见都要打这样的“擦边球”?!
我喟然长叹,竭力劝说自己。不是吗,本来就没有相约,我们毕竟不是“一家人”,也不是“嫡系亲属”,尽管以往关系密切,但茫茫这几年的真实情况,我又所知多少?而且,毕竟没有招呼,又怎么断定刚才那个美女姑娘真的就是她?
不过,不管怎么自我排遣,我心里还是怅怅不已。
于是,当晚在莫泊桑饭店的晚宴,尽管是包括了蜗牛在内的地道而又丰盛的法国大菜,我却因为无心无绪而品尝不出一点什么特别的滋味。
旅行是快活的事,旅行也最容易疲劳。前几天都是早早洗漱着枕便睡,但这天夜里,却怎么也睡不着。安静整洁的房间,换洗过的雪白洁净的床单和枕套,有一股淡淡的桅子花味,崇尚香水且种类繁多的法国,在诸如此类的铺陈中果然都有体现。
我却依然辗转多时而无法安眠。
胡思乱想中,纠缠于心的都是有关茫茫的一切。准确地说,应是有关她母亲和外婆的一切。
难道命运和人生经历也会随外貌遗传?茫茫的母亲和外婆,都是旷世美女,同时也都有着旷世美女的红颜薄命。
母亲早就告诉过我:二十年代末,茫茫的外婆,就曾以她的出奇“故事”和绝世美艳,曾教故乡的小镇天翻地覆。
……我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之中——
我掉入了一个深深的漩涡,浊水万丈,恶浪滔天,一艘黑色的铁壳船迎面开来,从我头顶隆隆开过,顷刻之间就要将我绞成肉泥。我不会游泳,周围没有任何可以救我之物,更不用说救我之人。
我伸手乱抓,可四下全是一片冰凉的水,我能做的,只是一声声绝望的呼喊!
我惊醒了。
心如撞鹿,冷汗淋漓。当明白自己刚才不过是做梦时,竟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惊喜。
故乡的老人总说人梦见水是好事,梦水,要发“水花财”。
是这样么?我常常梦见水,可它从来没有应验过。对我来说,梦常常是现实的一种反证,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叠而已。
我越发睡不着。在这时候,最好的方式是索性披衣坐起,让梦境回归现实,哪怕仅仅是回忆的现实。
“半掩门”母女
六十年代初,我踏上了人生旅程中的第一个驿站——青岛。
夜色苍茫中,我随着来接我的要成为我丈夫的滨声仓惶地走,高一脚,低一脚,细细的微雨中,两人共撑一把黑色的小阳伞,我的浅绿葡萄叶的花布连衣裙和脚上的布鞋,溅满了泥点。那情景,压根儿不像来结婚而是来逃难。
婆家在火车站附近。当我一脚迈进了一个大杂院时,这个原本很为我仰慕的胶州湾海滨城市居民区,却以一种我完全没有料到的面貌,呈现眼前。
婆家的大杂院是沿着一座大天井砌的四围两层楼,一门一窗便是一户,像蜂窝一样。夜深的幽微灯光中,一时看不清有多少户人家拥塞在这两层楼的院中。
第二天一早,我从婆家的窗户中,张望这一只只炊烟袅袅的“蜂窝”,愣愣地看着一个个在院内活动的身影。
婆婆和公公在鸽子窝似的楼屋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与物质有关的一切都贫乏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可是,生活中只要有一点点喜乐,仍会像连日的雨花一样四处迸溅。
穿着打补丁裤子和我结婚的滨声,只有脚上的鞋子是新的——那是我亲手做的。眼下的我和他,在喜洋洋的婆家,成了“富贵闲人”,傻乎乎而无事可为地看着两个老人里外张罗。
公公婆婆拿着凭“结婚证供应”的两斤喜糖,摆在炕桌上像数珍珠一样分成小堆,一边念叨着:陈家的、章家的、龚家的、邱家的、水果林的、烧鸡铺的……
喜糖的分发对象是大院中的邻居,“堆儿”的大小,是根据这家孩子的多少。
“真寒碜人,就那么几颗糖,他爹,待会儿给人家时你可得跟人说明白,不是咱不割舍的,一共就让咱买这么一丁点东西,唉唉……”婆婆不住唠叨着,一会儿从这堆上减下两颗,一会儿往这堆上增添一颗。婆婆摆弄停当后,听话的公公就用裁好的一张张红纸包好。
公公耳朵背,常常动用自己发明的“扩音器”——以一只手掌遮耳,才听得见人说话。但婆婆唠叨的内容他好像不用听也明白。突然,他想起了什么。
“忘了给班家吧?添上她一份……”
“给她?给那个‘半掩’家?”婆婆反问。表情和语气都表明:她不是疏忽。
公公很不以为然。“怎么不给?给!人家也是一户嘛……”公公说着,不由分说地从还没分完大堆里抓了一把。
“要给也不用那么多,她家又没小嫚……”看得出来,婆婆明显的不怎么喜欢这个叫什么班家还是半家的,她硬是从那堆儿里又扒拉下几块,一边咕哝说:“原都不够分……”
“你都不想想,班家的跟我们滨声家的还是浙江老乡哩!”公公见婆婆仍不肯通融,叹息一声,摔了手,扭头就出去了。
没多大一会儿,公公又转回来了,他的手中奇迹般地捧了一小包……糖!
这情景使大家都喜出望外。婆婆一个劲地追问公公是牺牲了家中别的什么才开来了这个后门?公公瞪她一眼,皱着眉,恼怒地低吼了一句什么。
我没有听懂。公公婆婆说的那些胶东口音很重的方言,我常常不能完全听懂。
婆婆不再咕哝,仍然将“班”家的那一份抓了出来,分门别类地放在一角。
寒伧而简朴的婚礼举行那天,大院里的孩子嘻嘻攘攘聚集到我们家门前,虽然每家已按份分发过喜糖,孩子们还是要到办喜事家的人家再抢几颗糖,这也是一种讨彩。喜笑颜开的公公,差点没让那帮晒得泥鳅似的蛮小子给掰坏了指头。
没来凑热闹的,只是班家。本要送去的糖,被隔壁邻居告知“她们娘儿俩出门了,到医院去了”而暂时搁置。
忙乱中顾不上许多细节。
三天后的傍晚,滨声正想带我到海边遛弯,公公曼声吩咐道:滨声,快把这给班家送去吧!都几天了……
我们顺着他努嘴的方向一看,终于瞥见那个小小的红纸包,依然静卧在壁橱上方。
丈夫一向很遵从公公的主张,大概觉得这几颗糖太小小不言了,迟疑而为难地说:这点点东西……
公公嗔怪地瞪他一眼,固执地说:不在东西多少,这是礼数,你和你媳妇一块送,好歹她们也是老乡……
“好吧,好吧……”
我糊涂了,小声问滨声:“这家人是姓‘班’还是姓‘半’?还有这么奇怪的姓……”我住了口,因为丈夫重重地按了一下我的手腕。
班家的木门与大院内多数人家一样窄小而破旧,轻轻一推就开。
进门后才发现窗边吊着一盏度数极低的灯,窗框旁虽然罩了一张白纸反光,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依然十分昏暗,好大一会儿,我才大体辨得清眼前的物事。
屋子虽小,却十分清洁,桌椅板凳全都揩得干干净净,就连板壁窗框也擦得纤尘不染。只是,屋子实在太小了,中间又被一张桌子、桌子又被一堆山也似的火柴盒子占据了全部地场,周围的许多物事好像都被遮掩了。
就从这堆小山也似的火柴盒中间,伸出了一个梳髻子的花白脑袋,大概没有想到是我们,班家的这个梳髻子的老女人“哎”了一声,连忙站起,热乎乎地手忙脚乱地一边招呼,一边试图给我们腾出坐的地方来。
滨声连忙表示不必客气,说明来意,放下糖就要走。
“多谢多谢,你爹总想着我们!”老女人忙着从壁角的床下抽出凳子,连连说:“忙什么呢,滨声,坐,坐呀,难得回来一次,就在我们这里嬉嬉一歇歇,嬉嬉一歇歇……”
“嘿,坐一会儿也不会矮了你,化了你,怕什么呢?!”随着话音,突然从我眼前亮起一道月光——一张雪白而姣美的脸庞,鬼使神差般从老妇人的背后,在一道半截的蓝印花布的帘子后边出现,一对水汪汪的杏眼在蓬乱的额发下,讥嘲地半眯着,飞速地射向我们,亮亮的眼瞳,在我身上逡巡了一圈又一圈,接着又用鼻子轻轻哼着。“到底是南方人,小模样真不错,嗯,这么小,够不够结婚登记的年龄?”
我惶惑地看着她,不知说什么才好。
她不理会滨声,突然又朝我说:“喂,你叫什么名字?知道么,没听你公公说么,你和我妈是老乡呢!不信你问问……嘿,滨声,现在是大教授了不是,架子大了,不爱搭理我们这小民百姓了?”说着,她又眯着眼在我脸上“剜”了一圈。“滨声,你可真有本事,骗得来这么俊的南方小媳妇……”
滨声脸一红,立刻期期艾艾,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与眼前的这个俊俏女子多说话,但又想不出托词马上告辞。
“人家是客人,婧婧,你这是做什么……”老女人沉下脸喝住了年轻女子,依然客气地招呼:“滨声,快坐快坐……”
滨声终于想出了借口:“哎哎,大娘,有个同学同我们约过了,让我们过去呢!不坐了,不坐了!”不会撒谎的他,连脖子都红了。
“拿什么架子,哼!”那个被老女人叫做婧婧的年轻女子一听,立刻摔下脸,像刚才一样飞速消失在那道半截的蓝印花门帘后边……
那老女人倒也不强留,立刻很解人意地说:“那是,那是,快去吧,别教人家等着,咱这儿离得近,早早晚晚都能过来嬉嬉的,跟你爹娘说,谢谢了,哎,那么惦记我们……”
走到门外的马路上,丈夫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大气。
我好奇极了,一百个问号霎时堆集心头。
那时的我,虽然已经发表过几篇小说,却不敢将这归结于小说家的敏感。
但是,关于“班家——婧婧”的一切,就此引我好奇顿生。公公、丈夫还有这个婧婧都说老女人和我是“浙江同乡”,更令我大感兴趣。从她明显的故乡口音和最后的那几句“嬉嬉、一歇歇”,我判断出这真是我们老家的方言,这么说,她不仅是我的大同乡,还可能是很小范围的老乡。
“滨声,我看,那个婧婧很爱你呢,她看你的目光,真像是无奈分手的情人似的……”
“什么话!”滨声涨红了脸,立即否认。“她对谁都是这样……哎,不过,我们倒真是初中同学,她比我低一届,是外来户,我上高小时,她和她母亲才搬到我们这大院……咱爹早就认识她母亲,是在大港码头认识的,爹那会儿在码头看仓库,大概是鬼子投降那时候吧?也许是稍早一些些,我不清楚,反正那会儿乱七八糟的,日本鬼子都在撤,那班大娘,哎,就是婧婧她妈,抱了个四五岁的女孩,对,就是婧婧,听说她妈当时是有意不肯上船还是被人拉下的,我也不太清楚,听爹说好像是被人遗弃了还是怎么的……嘿,她那时还会讲几句日语呢!原来她们是住在外头的,后来又遇见咱爹,才又搬到咱这个大院,这里的房租便宜。后来,咱爹退休了不是当着居民小组的什么委员么,见她们母女生活困难,就常给她母亲介绍个糊火柴盒子之类的活,挣几个小钱对付过日子……所以她妈总对咱爹有点感激涕零的,嘿,有时还惹得咱娘老大不高兴,你知道咱娘是小心眼……”
“这我知道。我到现在也没听清,她们是姓班吧?娘为什么叫她们是‘半掩’家的?”
“是姓班。婧婧的学名叫班小诺。嗯,‘半掩’么,就是,就是‘半掩门’,你知道吧?北方话,当然是不好的称谓,院子里的人都说婧婧母亲以前是不正派的女人,所以全大院的人都有点瞧不起她们,还说婧婧是外国种呢!……”
“真是这样?”
“乱猜罢了!”
“婧婧父亲呢?”
“不知道,我从没见过。反正她母女俩的行为有点神神秘秘的,也不和院子里的人多说话,咱爹可能有点知道底细,可咱爹是厚道人,从不多说别人……”
“这个婧婧长得真漂亮!”我由衷地赞叹,“你真傻,婧婧要是真和你找了对象,你可是艳福不浅!”
“什么话!她后来压根儿不上学了,我离家上大学后就不知道她的事,哪里会同她……”滨声很认真地辩白道:“我们这个大院几十户人家,邻居也不过是邻居而已,彼此有点知道,却不是知根知底的,不像你们南方小镇,上下三代都一清二楚,就像你在小说里写过的那样:‘小镇上传消息,比电报还快’……”
“别打岔。我是说,这婧婧的母亲,真是从我们那里过来的么?咱爹真知道她的来历和细情?”
“不,不很清楚的,我们这里,说是邻居,平日是谁也不管谁的闲事的,我只知道婧婧初中只上了两年就休学了,嗯,我和她,虽然同一个大院住,也在一个学校上过学,可十多年加起来没说过多少话……”
“这么假撇清干什么?”滨声着急分辨的样子令我好笑,我知道他这人不会说假话,但我还是要逗一逗他。而且,婧婧刚才的言行举止虽然有点尖刻,但她真的特别漂亮,说实在,我至今还没见过比她更俊美的姑娘。她母亲也是,这母女俩的眉眼五官,特别是那双得兼“凤眼”和“杏眼”之美的眼睛,朝人一望,真是风情万种,大有教男人们招架不住的勾魂摄魄的美丽。
我一点不夸大,这母女俩,真是美丽到了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地步,那班大娘虽是老人,按我们南方的美人标准,也够得上俊俏透顶,除了脸色稍过苍白外。可是,也许正是这出奇的苍白,才惹动我由衷的赞叹——因为,苍白和苍白关联的凄美,一向使我动心。
“哦,这婧婧和她母亲,长得可真是,是的,说像又不完全像,可都那么美丽,不,准确地说,是妩媚,我觉得婧婧有点特别……不,我更喜欢她母亲的那种清秀脱俗的、静静寂寂的妩媚,她年轻时准是个绝色美女……婧婧么,有点洋气也带点野气,没和她好,你真是呆犊一个……”我自言自语。
“哎,你问这问那,原来是怀疑……”滨声认真得又像生了气,等他明白我是在开玩笑时才如释重负地笑起来。“你也真是……怪不得说写作的人都有点小神经……”
“嗯,我问你,婧婧后来为什么不去上学呢?”
“当然是因为生活困难想早点工作吧。”
“你不是也享受助学金么?她为什么不去申请助学金呢?”
“这?我哪里知道……当时听说她好像去什么文工团了……”
“现在呢?现在她做什么?”
“我哪里知道?我不是也离家好多年么,听说好像也在码头的什么单位……
我沉默不语,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和想象中。婧婧和她母亲的出奇美丽和神秘身世,特别是她对人说话的神情,在我心里激起一片分外好奇的连漪……我突然想起来:她们母女之所以容貌姣美且又特别神似,还因为她们脸上都有一对大而深深的酒窝,不同的是,女儿的眼睛有一种撩人的妩媚,而母亲则有一颗美丽的小痣,俏皮地跳在左眉上……
美人微疵才是真美!
公公可能知点内情,但他耳背得厉害。平日,我们与他交流总要提着嗓门才能对话,就这,也常常被他听岔了意思。因此,除了肯定婧婧现在是在大港码头的下属单位上班以外,早已退休的公公也说不出有关婧婧母女更多的近况和内容。而小心眼儿的婆婆,却总是时不时的从左邻右舍的“小广播”中听到一些传言。不久前,她又听到了一个秘密,言之凿凿地说:前些日子婧婧母女去医院,是“老的陪着小的偷偷去做‘人流’了……”
为了证实自己说的没错,婆婆加重了语气:“老葛家的可是不会屈枉她的,你不知道人家老葛媳妇就在那家医院当护士长的,现在,满院的人都知道了,他爹,你没听说?我不信你真没听说……”
公公含混地应了一声,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婆婆乘机大发感慨:“什么样的娘生什么样的闺女,那娘儿俩,没治了,真没治了……”
我好像猜测到了一点什么。
因为居住空间窄小,大杂院的人家,总是将很多吃喝拉撒睡的私人生活家务内容展现在院子里。令我奇怪的是,这个大院惟班家母女例外。不知为何,她们很少在院子里出现,婧婧和她母亲也很少与别人打交道。这在一个连解手撒尿都在一个公用茅房的大杂院居住者来说,真是与众不同。特别是班大娘,整日在家忙着糊那如山堆积的火柴盒,足不出户。
于是,渐渐地,进出大院时,敏感的我,虽然时时感觉着楼下某个角落的门帘后,有双不无友好而略带哀怨的眼神的注视,但是,对神神秘秘的婧婧和她母亲的话题,却不能不随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进程而淡然。
日子飞逝,我们很快度完了半个月婚假而终于要离去了。这天傍晚,我照旧来到海滩遛弯,和往日不同的是,这天仅仅是我自己——滨声遵公公吩咐到亲戚家送什么物件去了。
半月下来,我对这片海滩已是熟门熟路,特别是那处在黄昏时分露出海面的礁岩,早已成了我每天晚上的消闲之处。
那个年月,青岛最教我眷恋的,就是蓝天下的大海,就是这海天一色的有着黑森森礁岩的海滩。
海滩寂寂,蔚蓝色的海浪,裹着白花花的裙边扑将上来,就像是害了单相思的女孩,执拗地一次又一次地扑向意中的情人,亲昵地不厌其烦地拥吻着,她一无所有,唯有这拥吻是如此固执而甜蜜……
造物主对人还算公平。这处近在咫尺的寂静而不无美丽的海滩,就是对世世代代居所拥塞的人们的补偿吧。要是没有它,我可怜的住了一辈子大杂院的公公婆婆们,不是连个透气的地方也没有么?
“嘿,好悠闲呀,看什么呢?”身后传来熟悉的语声。
是她,婧婧!弹跳般走近来的婧婧,步子轻盈又优美。
夕阳中,她那略略苍白的脸庞透出了一抹粉茸茸的浅红,那张美丽的脸于是更加千娇百媚。由于夕阳的点染,她的头发泛出一圈似金非金的浅棕,这种颇显华贵的发色在如今极为流行,年轻的时髦女孩,差不多十之八九都去染过这种“外来色”。可我敢说,从没有一头秀发,能够与我当年在海滩看到的婧婧相嫓美,那是蓝海衬出来的真正的自然美色。
我从礁岩上站起来,面对她,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有点惶恐。
她轻盈地跳身过来,一坐到我身边,就不由分说地一把将我按了下去。
“坐嘛,再坐一会儿。滨声没同你一起来么?他怎么不陪你?真是的!说到底,山东人都是老粗,指望他们知冷知热地疼媳妇,没门!”
我一时语塞。说实在,至今我与她还没有正式交谈过,我略显窘迫地微微一笑,不知道与她说些什么才好。
“你们快走了吧?明天就走?到哪里?还去河南?内乡?这样的名字?嘿,什么鬼地方,听都没听说过!你怎么会答应跟他去那样一个地方?别走了,青岛多好呀,青岛再差也是大城市,你跟他去那儿干什么?要我,宁肯在青岛要饭也不去!”她滚珠连串地说着,脸上掠过因话语而改换的表情。那表情也因她急速的语声飞快而生动,杏仁般的眸子在暮色中闪闪星亮,那张美丽的脸,在斑斓的夕照中简直是五彩流光。
对于她的话,我依然不知如何回答,也无法回答。而且,我发现,婧婧说话语速极快,无需或者可以说根本无视对方作什么反应,那双瞳仁乌亮眼白有点泛蓝的眼睛灼灼地瞪着你,眼神却不住地游动,我忽然感觉她好像有点病态,至少眼神透露出某种病态的信息。
我为这个发现吓住了,心情突然一阵紧张。
“喂,我说,滨声对你很好吧?他可是个好人,我们山东人就是爱讲义气……”她亲亲热热地挽着我的肩膀,唇线分明的菱角嘴凑近了我的耳朵,轻轻吹出的气,教我的耳根痒痒的。“你知不知道,我和滨声原来很要好哩,要不是他毕业分配去了那个鬼地方,我一准会嫁给他!真的,前些年,我可是真心真意看中了他,他是我少女时代的第一位白马王子,可滨声这人有点‘潮巴’,真的,大‘潮巴’一个,我对他动心思,他一点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时,追我的男同学都可以编成一个排了,他们成天为我打架,我们的一个音乐老师,为了我都差点跳楼自杀,你信不信?”
我想,我应该信。
她那么近近地挨着我,我才发现:要说婧婧也有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她虽然脸色很白,但脸颊和鼻翼两旁有着一些细小的雀斑,当然,若不是近观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我随即想起了一句俗话:美人可比美玉,白玉无瑕,有微疵的美人却比无瑕的白玉更耐看。她的这些细小的雀斑,好像就是为了反衬她的美白,就像她母亲眉角的那颗小痣,不但无损于美丽,还增加了许多妩媚。
面对她滚珠连串的表白,我不能一言不发,于是便点点头。“是的,婧婧,你很漂亮……”
婧婧眼睛一闪,开心地笑了起来。“是么,我真像你们南方女孩那样漂亮?嘿,你知不知道我们大院里那些人坏得很,他们给我起了许多外号,你可别听他们瞎掰乎,嗯,我们这大院,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些混账王八蛋!也就你们家,嗯,就你老公爹和滨声是好人,你知不知道,有次滨声为保护我,还曾跟一个想欺负我的小流氓打了一架,门牙都差点打掉了!真的,他没有对你说过吧?他肯定不好意思说的,你可别问他……”
我当然不用问也不会问。婧婧虽然坦率得令我吃惊,但我也推断出有一些“情节”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真实,例如滨声为她打架和“门牙”之类的事。
我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喂,我问你,滨声他是不是结婚当天就……就对你‘那个’来着?我们山东人,一个个人高马大的,又那么大岁数了结婚,还不是……急猴儿似的,是不是……”
她都说些什么呀……我的脸红到了耳根,不能不站起身来:“对不起,婧婧,我得回去了,今晚还得收拾行李……”
大概因为我的矜持,太辜负了她的美意吧,婧婧有点着恼,立刻很不友好地甩了手,掠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背转身子,两手抱膝,语气冰冷而不耐烦:“你这人……好好,走吧,走吧,我还有约会……”那神情,霎时间就与刚才判若两人。
勺港的婼婼
奈尔小姐早上准点来到。我们一块吃了早餐后,便驱车前往展览中心所在地。
这次出访法国,是省对外友协的一项文化交流的任务,我们将在此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首先要举办一个包括书画展出、然后是音乐舞蹈演出的“西子文化节”。
“友协特邀理事”是我最近的一个“虚职”,所以我当时的身份是代表团的“顾问”。我是为了搜集眼下要写的一部传记文学的资料接受这项兼差的,书中主人公曾经在法国生活多年,所以非来这儿不可。因此,这项兼差于我,是一举两得。
展览中心和卢昂所有的场所一样,美丽而洁净。展馆在花园中央,被一片草地簇拥,绿茵茵的草地,嫩气生香,远远望去,白色的馆舍就像碧绿的江面飘着一片白帆。
早在我们抵达前,奈尔小姐已替我们选好这个展览场所。她说我们带来的字画,昨天也都在室内悬挂完毕。这一次,我们这个团所带的,大多是文联和画院提供的我省当代书画家的作品,虽不属国家列名禁带的大家名作,却是非常有水准的。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了奈尔小姐的精心,她总是时时表示对中国文化懂行和亲昵——她让人在展厅门口上方,横悬了两条金色的龙,展厅两侧又吊起了四盏有着双喜字的大红灯笼,对于一个书画展览来说,这装饰称不上精致更不能算协调,但却有中国式的喜气洋洋。
书画展虽然只是整个活动中的一项,但参展的书法绘画,大多是我省首屈一指的年轻美术家的作品,这其中,尤以“水乡画家”之称的立舟的作品——《水乡江南·四季系列》最为醒人耳目。立舟因独特的表现手法名声鹊起,多年来在全国美展以及其他活动中屡屡获得奖项。
“西子书画展”在一片掌声中开幕。
如果不是眼前的“观众”多是金发碧眼,我并没有感觉这是在国外。虽然,刚才出了点差错,一些细节安排也不是那么合规合矩,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像模像样的,起码展出的作品很能体现中国书画的品位。因而,虽然举办地是在法国的卢昂,我的感觉好像是在国内的某个城市又一次歆享了中国文化的大餐。
向以浪漫著称的法兰西,能否领略中国“西子”文化的别样情韵呢?
中西文化的不同在细节中也时时显现——他们剪彩用的是一条一指宽的细带而不像我们大手大脚的整匹红绸红缎;主持人的开幕词没有虚夸和客套而只是一两句很幽默风趣的“介绍”;而观众当然更不一样——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多是来者如意的样子。有几对看得一时兴起的年轻情侣,看着看着,就旁若无人地相拥而接起吻来。
法国人在任何时候总有无限的浪漫。
我们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则来自省文艺界的四面八方,有几位是音乐舞蹈界人士,他们的展演节目,在另一个剧场安排,包括开幕式。因为难以分身,我和作曲家出身的团长各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与对方一起尽量安排好这次画展。
访问中的参观,无疑是代表团最感兴趣的。
天淡云低,细雨飘洒,卢昂的秋天竟如杭州之春,时晴时雨,极有诗情。
细雨如诗中,我们在带路人的引领中走向一所博物馆,那馆舍无例外地和这座城市一样古老而整洁。除了第一展厅的橱窗摆了一些古物外,其余无例外是宗教内容的油画。
刚刚走出博物馆,换了一身米白色衣裙的奈尔小姐,手持一柄长伞,像一只秋风中飞翔的白鹳,脚步飞快地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发丝上落满雨珠的奈尔,指着天色,皱眉耸肩地叹气说:天气太糟糕了,她想稍稍改动我们的参观内容——问我们是愿意接着冒雨去看当地的一些纪念地还是去逛商场?
当我听说贞德的纪念雕像以及被处死的行刑场就在附近时,不由得惊喜万分。我直截了当地对奈尔表示:对于我来说,如果能够看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地,哪怕再淋雨也没有关系,至于商店那是可去可不去的。
说话时,我心头旋风似的刮过了昨晚的梦境,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的愿望,真的完全是由于那个世人所敬仰的贞德,还是别的什么。
奈尔听清了我的要求后,诧异而不无惊喜地说:她非常尊重我的意愿,因此,她可以马上去找一名懂法国历史又能说中国话的大学生来陪我,这样,就能尽情介绍有关贞德的美丽而壮烈的史迹……奈尔再三说,她还认识好多“中国通”,一定可以找到我所需要的陪伴者。
我知道她误会了。我不过是一名游客而并非专门的研究者或专家,我诚恳谢绝了她的好意。我说:绝对无需再找什么人专门陪我,如果其他人都愿意逛商店,我就自个儿去哪个地方转一圈就行。我请她放心,我说我还知道下一步的集合地,我绝对会追上她带领的那支对法国商店特别爱好已经走得松松散散的参观团。
我拖着走得发酸的脚,在街角的长条木凳坐下,凝视着离我咫尺之遥的贞德雕像。
思绪一如秋风翻卷。此时,我才明白:刚才,与其说是被贞德之死的壮烈所感,还不如说是她那“处死方式”的惊世骇俗使我感怀不已——在中世纪的这个小城,一个曾为国家赴汤蹈火的年轻女子,在大庭广众中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
历代中国女子,与此壮烈死法相似的,都有谁?
哦,秋瑾,大义凛然的秋瑾当然算一个。毫无疑问,她一直是我无比敬崇的女侠。秋瑾慷慨赴死的一幕,曾使为其作传的我热泪涟涟不能自己。
其他呢,当然,当然还有很多,古今中外许许多多革命烈士……
且不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她们,大家都熟悉。我想的是小人物,想想那些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惊世骇俗的普通百姓平凡女子……
就此来说,茫茫的……对,茫茫的外婆也属这样一个女子!
怎么又想到了茫茫?至此,我才明白;今天的恍惚的思绪,全在于昨夜不宁的梦境。
不不,也许该说,全在于昨日与茫茫不期而遇而又未曾真正相见。
结婚两年后,我回到老家分娩。